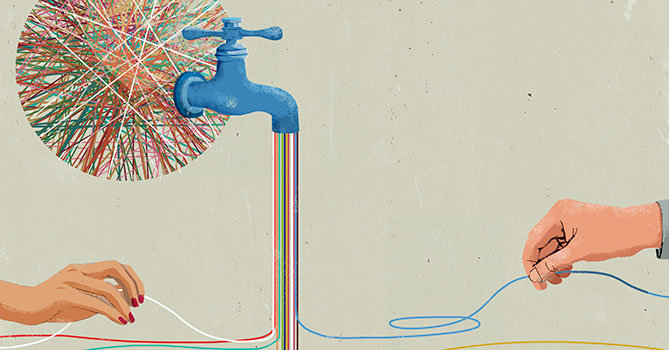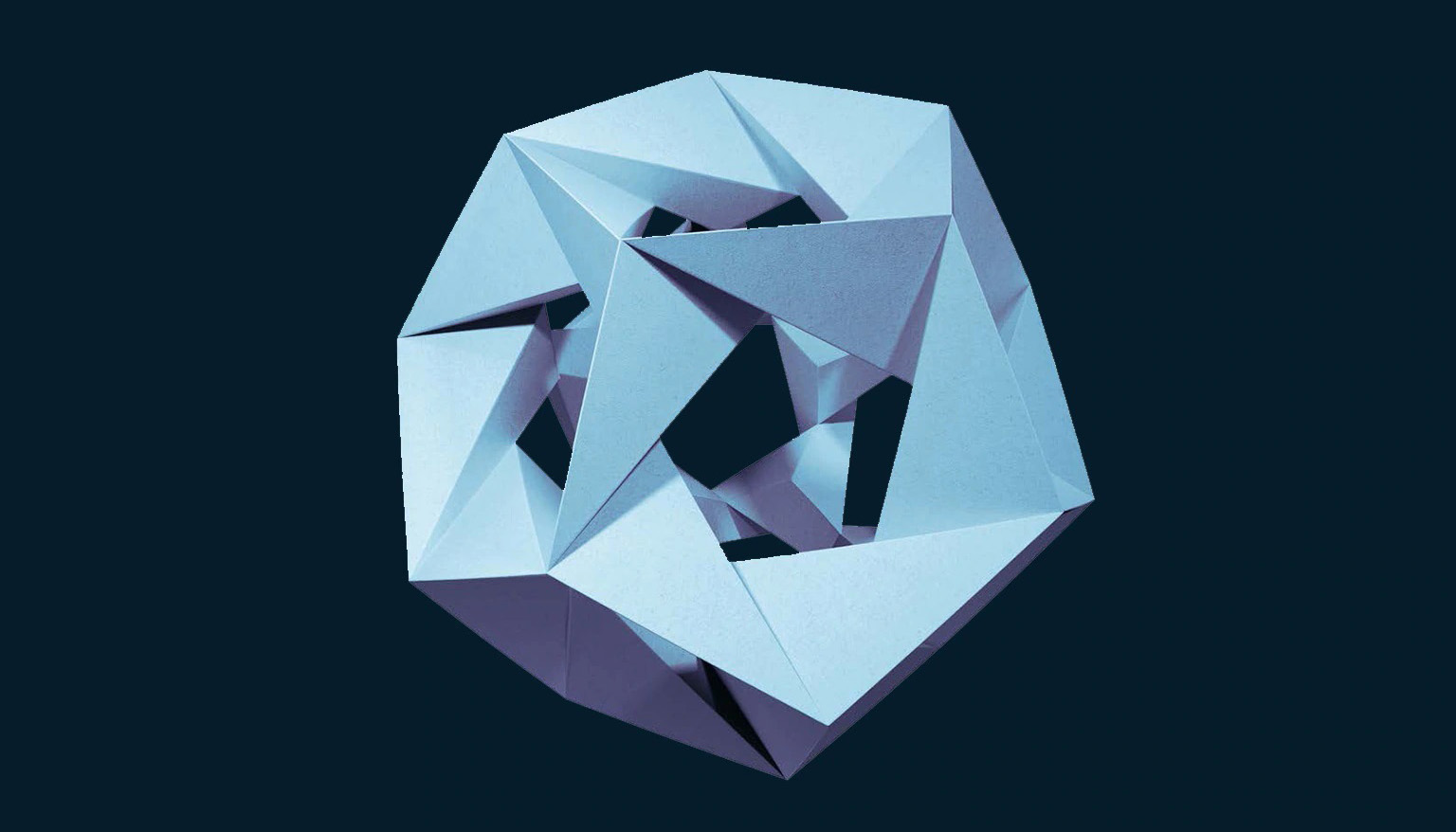Eric Beinhocker , Nick Hanauer
资本主义正在经受抨击。2008年金融风暴期间,诸多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遭遇发展停滞,再加上财富分配不均恶化,我们原本深信的管理一个公平和高效的社会所仰赖的各种机制遭受到了普遍的质疑。
很多企业领导者对此的看法摇摆不定。他们注意到市场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尤其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国家。更近一点来看,资本主义使新兴经济体中的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巨大的历史成就,人们仍很容易陷入这样的担忧:当今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是不是在某些地方出问题了。
本文要论证的是: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造就历史发展和繁荣的主要源泉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多数人都没有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如何以及为什么能运转得这么成功。试做一个类比,我们的祖先知道恒星和卫星是在天空中运行的天体,也提出了各种用来解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的理论。但直到哥白尼提出太阳而非地球才是太阳系的中心、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人们才算真正了解了这些天体运动的方式和原因。
与此类似,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依赖的传统经济理论,误导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运作机制的认识。只有代之以更先进的现代理论,我们才能树立完善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更深入的见解。
两种经济学说:木马说对野马论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范式,即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给人们描绘出了一幅狭隘、机械的资本主义运作图景,强调市场和价格在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中的作用。众所周知的故事是:理性、自利的公司努力实现利润最大化;理性、自利的消费者努力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这些参与者的决策推动着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价格是固定的;市场是透明的; 资源配置的方式在社会意义上是最佳的。
不过,在过去几十年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一些最基本的假设开始被瓦解。行为经济学家已经积累了海量证据,证明真正的人不可能表现得像一个完全理智的经济人。实验经济学家提出了关于效用之存在的蹩脚问题;而这本身就有问题,因为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正是利用这一工具来证明市场是如何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实证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了其中的异常,这说明金融市场并不总是高效的。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模型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也非常糟糕。
英格兰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Andy Haldane指出,传统理论将经济视为摇动的木马,一旦受到外力扰乱,会先摇摆一阵,然后才返回到静态平衡状态,这是可以预见到的现象。但是Haldane指出,我们在真正的危机中看到的却更像是一群野马,一旦有什么事惊吓到马群中的某一匹马,这匹马会踢到另一匹,很快整个马群就会以一种复杂、活跃的方式狂奔(注释1)。
在危机发生前数年,一种新的经济学观点逐步萌芽,而危机爆发后则开始蓬勃发展(注释2)。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是一个由高度多样化的家庭、公司、银行、监管者和其他机构之间不断变化发展、相互作用的网络,与其说它像一匹摇摆的木马,倒不如说与Haldane的野马群更相似。经济——一个复杂、活跃、开放、非线性发展的系统——相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所效法的机械体制,更接近于一个生态系统。这一新兴观点的影响和意义,目前才刚刚开始被发掘。但我们二人认为,这对人们如何思考资本主义和由其带来的繁荣的本质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很显然,这个观点大大撼动了我们对市场为何运行、如何运行的看法,不管是其分配效率还是其在推动创新方面的效能。这一观点认为市场是发展变化的系统,每天都同时进行着数百万个实验,目的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换而言之,资本主义最关键的角色不是分配,而是创造。今天,与1800年相比,数十亿人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能更高效地对19世纪的经济资源进行分配。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是因为我们有了救命的抗生素、室内厕卫、机动车、获取大量信息的渠道,以及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如果还不是所有人)都可获得的众多的技术和社会创新成果。资本主义的天赋在于既能创造解决人类问题的激励机制,又能使这些解决方案得到广泛普及。而且,繁荣的定义正在于对人类问题的解决,而非金钱与财富。
重新定义繁荣
我们大多数人都凭直觉认为:钱越多,社会就必定越繁荣。2013年美国的户均可支配收入为38,001美元,而加拿大为28194美元(注释3); 人们因此认定美国比加拿大更繁荣。然而,只需一个简单的思考实验就能证明把繁荣单纯等同于拥有金钱是错误的。设想你拥有美国一般家庭38001美元的收入,但是却和亚诺玛米人(Yomami)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生活于巴西热带雨林深处,与世隔绝,靠狩猎和采集维生的部落。你很轻易地就能成为亚诺玛米族最富裕的人(他们不用钱,有人类学家估计他们的生活标准大概接近1年90美元),但你可能仍会觉得自己比一般美国人更穷。即便你修好了小屋,买了村里最好的篮子,享用了他们最好的美餐,但你所有的财富却无法给你带来抗生素、空调或一张舒服的床。而即便是最穷的美国人通常也拥有这些重要的生活元素。
因此,人类社会的繁荣不能单纯地以货币来衡量,比如收入或财富。社会的繁荣是针对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的积累。这些方案有平淡无奇的小窍门(比如怎样使薯条更脆),也有更根本、更重要的大发明(如致命疾病的治愈)。最终,对社会财富的衡量将取决于其能解决多大范围内的问题,以及社会成员如何能获得这些解决方案。在现代化的零售商店里,每一件物什都可被视为解决某一类问题的答案——如何吃、如何穿、如何娱乐、如何把家变得更舒服,等等。我们能获得的解决方案越多、越好,我们的社会就越繁荣。
关于增长的新定义
GDP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近来广受诟病,但通常我们仍会以GDP来谈增长。也有很多观点认为,GDP是造成环境破坏、无偿工作、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发展的原因。
在我们看来,GDP作为衡量标准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无法必然地反映出增长如何改变大多数人真实的生活体验。以美国为例,GDP在过去30多年翻了三番多。虽然这些增长主要集中在高收入阶层,但多数人都从技术进步中获益(如更安全的汽车、新的诊疗法和智能手机等)。不过,增长也带来了其他一些变化,伴随而来的是意外的后果(比如一周七天、全天候处于连通状态让知识型工作者备感压力等)。对多数人来说,生活到底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糟了呢?增长带来的成果是如何分享的?GDP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增长的概念很重要, 那它应该体现真实的生活体验的改善。如果社会繁荣的实际衡量标准在于能否获得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增长就不能简单地以GDP的变化来衡量,而必须以获取人类问题新解决方案的速度来衡量。
例如,人们前一天还在担心由于鼻窦感染造成死亡,第二天就获得了救命的抗生素,这就是增长;前一天还热得窒息难耐,第二天就能享受到舒适凉爽的空调,这也是增长;从长途跋涉到开上汽车以车代步,也是增长;从需要去图书馆里查阅基本信息到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立即获取全世界的信息,更是增长。
对于“增长”最好的定义是针对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质量和可获得性上的提升。待解决的问题重要性各不相同,因此新的增长观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找到癌症的一种治愈方法可能胜过很多其他产品创新。但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是改善生活过程的真实体验。
这不同于增长的其他衡量标准。例如,研究显示,幸福快乐与GDP增长并不一定相关——不丹(Bhutan)甚至发明了著名的国民幸福总值( GNH )指数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类似的,联合国根据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有关人类潜能和自由的理论制定了一套人类发展指数 ( HDI )。而我们则建议在GDP和上述这些标准之间提出一个新的标准。像GDP一样,这个新的标准旨在定义物质繁荣;但与GDP相比,它也是一种更有意义的考量生活物质标准的方法。
那我们有办法衡量对于人类问题解决方案的出现和获得的速度吗?虽然对此种衡量手段尚未尝试,但我们相信是可能的。通货膨胀一般情况下是根据家庭消费“菜篮子里”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化来衡量的,同样的,也可以看这个菜篮子里的实际内容随时间发生的变化,或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收入水平间的差异如何等。人们获得了什么类型的食品、住房、服装、交通、医保、教育、休闲和娱乐呢?
重新定义资本主义
如果繁荣是由不断解决人类问题而创造的,对社会而言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最快地为最大数量的人解决最多的问题?而资本主义正是这方面的天才:在寻求解决方案方面,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仍在发展进化的制度。
寻找人类问题的新解决方案很少情况下是容易或明显的,若不是如此,它们或许早已被发现了。例如,解决人力交通问题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可选方案有很多:自行车、三轮车、单轮车、滑板车,等等。人类凭创造力发展出了各种各样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但有一些不可避免地比另一些方法更好,我们需要一个能去粗取精的流程。此外,我们也需要一个能使好的解决方案为人们广泛获取的流程。
资本主义是一个催生这些流程的机制。这个体制为每天数以百万计为解决问题开展的实验提供激励,它引入竞争以从中选出最佳方案,并为最佳方案实现最广泛的普及和获取提供动力和机制保障。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会缩减或消除那些不那么成功的方案。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把这一发展过程称为“创造性的毁灭”。
这种正统经济学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有效运转的原因就在于它的高效率。然而在实际中,资本主义的巨大优势在于其解决问题方面的创造力和有效性。正是这种富于创造力的效用必然地导致其效率极度低下,像所有的进化过程一样,资本主义这种机制有着先天的浪费本性,从每年大量的生产线、投资和创业亏损就能证明这一点。成功的资本主义需要的是风险资本家威廉•詹韦(William Janeway)所说的“熊彼特式的浪费(Schumpeterian waste)”(注释4)。
企业的角色
每个企业的建立都基于一个如何解决问题的想法。把好的点子转化为产品和服务,有效地满足快速变化的人类的需求,大多数企业都可如此来定义自己。因此,企业对社会的最关键的贡献就在于将点子转化为解决问题的产品和服务。
这听起来很简单而且显而易见,很多企业的管理者会说:“没错,这就是我们所做的。”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不是那些正统理论对企业应该做什么的定义。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基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些学术研究提出,股东价值最大化是企业唯一的目标。这些教授们说,如果公司照着这一目标做,就能实现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这固然矫正了以往机制中的一些缺陷,最显著的是赋予股东权力以牵制那些只顾做大自己的“商业王国”而不顾经济回报的首席执行官们。
但也有人认为,将创造股东价值提升至企业主要目标的高度所依据的其实是一个假命题,即认为资本是经济中最稀缺的资源,而事实上知识才是真正稀缺的资源,是解决问题的最关键要素(注释5)。这造成短视地关注季度收益和短期股价波动,更造成长期投资的下滑。(注释6) 就在不久之前,人们的态度与之截然不同。回到繁荣发展的20世纪50年代,如果我们问一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第一个回答很可能是:“为客户提供最优秀的产品和服务。”之后,他可能才会说,他的工作还包括照顾企业员工、创造未来增长所需的利润,然后才是为股东带来合宜的、有竞争力的回报。
我们认为重新将企业视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者而不仅仅是为股东创造利益回报的工具,能更好地描述企业真正在从事的工作。这有助于企业高管们更好地平衡他们需管理的不同相关人之间的利益,同时也有助于企业转回到长期投资激励——毕竟鲜有复杂的人类问题能在短短一个季度内就得以解决。
这并不是说股东或其他所有权人不重要。但为这些人提供与其他企业相比更具竞争力的回报是企业成功与否的边界,而非其存在的目的。毕竟,活着的边界是获得足够的食物,而活着的目的远不止是为了吃。
有些公司已经从这些层面来思考问题。比如,谷歌公司将自己的使命确定为“整合全世界的信息,使人人得以访问并从中受益”——这是一个有关为人类解决问题的阐述。此外,谷歌还有一个出名的举动,就是拒绝提供季度财务报表。
重新定义政府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是高效的,有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内在本性,而且在管理干预最少的情况下运作最有效。然而,在现实世界里这种完美的市场似乎并不存在。不仅如此,这一观点忽视了资本主义有解决人类问题的天赋,也必然有其黑暗的一面:在解决某个个体的问题同时可能给其他个体带来麻烦。
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政治经济学谜题:经济体制如何解决矛盾、分配利益?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衍生产品也许能帮助公司的财务主管解决风险控制的问题,也许能让银行家发财,但也可能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与此类似,食用高脂肪食品可能满足一些人在千百年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下意识的欲望,但也可能造成动脉阻塞等这些新问题,而且会因个人未来的健康费用而给整个社会增加负担。
区分某种经济活动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制造问题是个挑战。谁又持有道德上的裁决权呢?民主是人类迄今为止提出的维持资本主义内在平衡、应对其缺点的最佳机制。民主用来解决其内部不可避免的矛盾的方式保证了最大的公平和合法性,也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的各种诉求。
把繁荣视为解决方案,这有助于解释民主因何与繁荣高度相关。民主制度确实帮助创造了繁荣,因为在某些方面的做法优于其他制度。民主国家倾向于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经济体,让更多国民既能成为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也能成为其他人提出的解决方案的消费者。而且,在应对某种经济活动到底是产生了更多问题还是提供了更多解决方案这一矛盾上,民主国家也提供了最佳方法。这是很多(虽然并非全部)政府监管规定设立的目的所在——鼓励解决问题的经济活动,同时限制制造麻烦的经济活动——从而增进社会的互信和合作。
生意人常常抱怨被监管——确实也有很多规定设计得很粗糙,甚至毫无必要——但事实上,解决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需要基于良好的监管体制才能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合作。很显然,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体正是良好的监管与自由市场的完美结合体,但凡监管不力、无政府主义泛滥,这样的经济体普遍是贫穷的。
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诸位理解了资本主义通过其解决方案来为人们的生活创造真正的繁荣,而我们找到解决方案的速度即体现了真正的经济增长,那么我们也就能清楚地明了企业家和企业领导者既是创造社会繁荣的功臣,同时也责无旁贷地承担着创造社会繁荣的重任。但对企业贡献的标准衡量指标,即利润、增速、股东价值等并不是什么好的参数。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在于创造和提供能实实在在改善人们生活的产品和服务,同时提供就业机会,让人们有获取其他产品和服务的经济能力。这确实是基本的道理,但我们的经济理论和指标并没有遵循这一基本原则。
如今我们以金钱和财富作为成功的标杆,此种文化并被一些大行其道的所谓理论强化。假设我们转而为那些能解决人类问题的创新方案而庆贺。设想我们在派对上,没有人问“您从事什么工作?”——这是一个借以了解人家赚多少钱、处于什么阶层的代码——而是被问“您解决些什么问题?”无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还是我们的社会都会变得更好。
作者简介:
Eric Beinhocker, 现为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新经济思考学院的执行董事,原为麦肯锡华盛顿和伦敦分公司员工。 Nick Hanauer 是一位企业家、风险投资家和作家。本文由同名文章改写而成,最先发表于Democracy : A Journal of Ideas (《民主诸论》)第31期,2014年冬,democracyjournal.org。
注释:
1.Andy Haldane是在2013年11月11日由英国财政部主办的一次活动上发表演讲时谈及这一观点的, 演讲题为
“Teaching economics as if the last decade mattered.”(《教授经济学,好像过去十年很重要》)。
2.参见 Eric D. Beinhocker所著的 The Origin of Wealth: Evolution, Complexity, and the Radical Remaking of Economics,(《财富本源:经济效益的发展变化、复杂性和彻底再造》),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Eric Liu 与 Nick Hanauer 合著的The Gardens of Democracy: A New American Story of Citizenship,the Econom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民主花园:有关公民、经济、政府角色的新美国故事》),美国萨斯克奇图书公司2011年版。
3.经合组织的“美好生活计划”(Better Life Initiative),《经合组织美好生活指数:国家报告》2013年,oecd.org.
4. 威廉•詹韦(William H. Janeway)著:Doing Capitalism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 Markets, Speculation and the State(《创新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市场、投机与国家》),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Clayton M. Christensen 与 Derek van Bever 近期在合著中对资本的稀缺性提出了质疑,参见“The capitalist’s dilemma,”(《资本家的困境》),《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6月, hbr.org。
6.有关股东价值最大化所未能预料到的后果,参见Dominic Barton 与 Mark Wiseman合著的 “Focusing capital on the long term,”(《侧重于长期资本》),《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2月, hbr.org。